茹诗瑶评《失去伊斯坦布尔》︱“帝国主义者”的多重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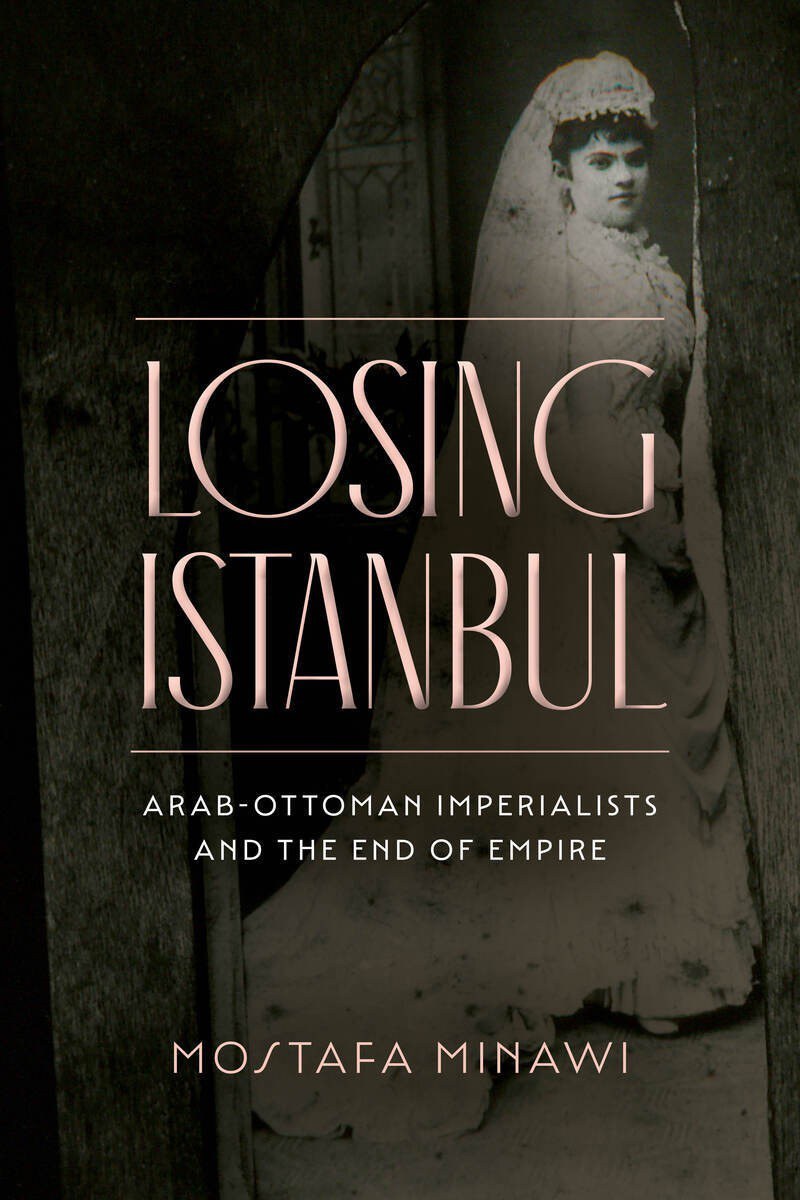
Mostafa Minawi: Losing Istanbul: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当帝国走向终结,昔日的政治精英们又当何去何从?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曾试图最后看一眼他所失去的那座城市的城墙;然而,这不大可能 —— 因为车窗的帷幔紧闭。只有他的一个年幼的儿子设法从窗帘的缝隙中投去了最后的一瞥,眼中满含着悲伤。”在《失去伊斯坦布尔: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主义者与帝国的终结》(Losing Istanbul: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下文简称《失去伊斯坦布尔》)一书中,历史学家穆斯塔法·米纳维(Mostafa Minawi)教授向二十一世纪的英语读者们“转播”了这一组细腻、伤感的历史镜头: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奥斯曼苏丹,在列车启动前的漫长等待中,度过了离开伊斯坦布尔前的最后时刻。
穆斯塔法·米纳维教授曾经就读于纽约大学历史系和中东与伊斯兰研究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史,不仅关注帝国的南部边境、北非与西南亚行省,同时也融合了全球帝国史、殖民主义史与外交史的广阔视野。他的第一本专著《奥斯曼帝国的非洲争夺战:撒哈拉与汉志地区的帝国和外交》(The Ottoman Scramble for Africa:Empire and Diplomacy in the Sahara and the Hijaz,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是其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之外,米纳维教授对于投身“公共史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仅为知名科普频道TED-ED的动画短片《奥斯曼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配音解说,还参与了纪录片《乘坐火车游览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 by Train)的录制。他于2022年出版的新书《失去伊斯坦布尔》一经问世便迅速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荣膺2023年度北美中东研究协会(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MESA)颁发的阿尔伯特·胡拉尼图书奖(Albert Hourani Book Award)。
在大量使用阿拉伯语史料、主要关注阿拉伯行省的奥斯曼史研究当中,家族史始终是一个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备受历史学家青睐的题材。比如,穆哈迈德·瓦尔迪 (M’hamed Oualdi) 在 《帝国之间的奴隶:一部北非的跨帝国史》(A Slave Between Empires: A Transimperial History of North Afric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0)一书中,以一桩家族遗产的纠纷案件为核心,揭示了不同行为主体如何在北非殖民体系下的“多重法律空间”中灵活运作,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简·海瑟薇(Jane Hathaway)的研究聚焦于埃及地区的卡兹达勒家族(Qazdağlıs),重点探讨该家族如何借助禁卫军等级体系、政治联姻、商业网络以及与宫廷太监的联盟等手段巩固其权力与地位。海瑟薇指出,以卡兹达勒为代表的政治家族并不是马穆鲁克时代的重现,而是一个具有鲜明“奥斯曼特质”的历史现象;广泛的精英联系对于维护、延续一个家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s in Ottoman Egypt:The Rise of the Qazdağlı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相较于以上这些研究,米纳维教授把“窥视”家族变迁的长镜头从地方转向了帝国的行政中枢伊斯坦布尔,聚焦于出身于大马士革名门望族——阿宰姆扎德 (土耳其语:Azmzade; 阿拉伯语:al-Azm)家族——的两位著名成员:莎菲克· 穆阿亚德·阿宰姆扎德(Shafiqal-Mu’ayyad Azmzade,1861-1916)和萨德克·穆阿亚德·阿宰姆扎德 (Sadik al-Mu’ayyad Azmzade,1858-1910)(下文中简称莎菲克和萨德克)。
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讲述了莎菲克和萨德克的早年经历。从家庭关系上看,莎菲克和萨德克是一对叔侄,二者的年纪相仿,实际上属于同一代人。因此,在接受教育的路径上,莎菲克和萨德克的经历也十分相似,先后在大马士革、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贝鲁特等地求学。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莎菲克和萨德克都离开了家乡大马士革,定居伊斯坦布尔,担任行政中心的帝国官僚。除了这两位主人公以外,本章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他们的社交生活,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精英文化与多元主义。第二章聚焦莎菲克与萨德克的职业生涯。一方面,他们算得上是精明能干的国家官员,对于奥斯曼帝国怀有强烈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他们也经常把手中的政治资本当做筹码,以权谋私、捞取个人利益。例如,莎菲克通过一系列社会网络与权力运作,成功解决了涉及家族利益的土地纠纷、刑事案件,甚至是针对他本人的指控。相较于莎菲克的贪污行为,萨德克在1893-1897年间的政治活动更直观地折射出帝国统治的“阴暗面”,其中包括他参与处理的贫困社区的霍乱,以及针对帝国东部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第二部分主要包括了第三到六章。这一部分的主人公是萨德克,主要内容围绕着他丰富的外交经历展开。第三章叙述了1888-1903年由萨德克承担的三次外交任务,其中包括1888年陪同俄国大公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Sergei Alexanderovich)访问黎凡特地区、1898年被派往德国柏林,以及二十世纪初代表政府前往俄罗斯、克里米亚以及奥斯曼巴尔干地区。以上的这些外交活动,无一不密切关联着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帝国内政外交上的一连串重大事件:1877-1878年俄土战争、德-奥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巴尔干地区日益动荡的政治局势。不停转变的政治定位、文化环境与地理空间深刻地塑造了萨德克的世界观,迫使其适应、中和不同的“惯习”(habitus)。接下来的两章主要透过萨德克的两本游记——《撒哈拉游记》(Afrika Sahra-yı Kebiri’nde Seyahat)和《阿比西尼亚游记》(Habeş Seyahatnamesi)——深入剖析了这位奥斯曼官员对“他者”(Other)与“自我”(Self)的身份认知与界定。1895年,萨德克受指派到撒哈拉地区,其主要任务是观察、协商以及提出政策建议,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在利比亚沙漠中,萨德克遇到了和他一样操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在旅行笔记中,他却有意识地把对方构建为一个熟悉的“他者”,称之为“土著”(natives)、“贝都因人”(Bedevi)而不是“阿拉伯人”(Arap),并刻意与之拉开距离 —— 即使这个“他者”与他共享同一套母语、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忠诚。在一个与自己的语言、宗教甚至文化密切相关的地区旅行时,萨德克并未提及任何相似性或熟悉感,这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实际上,他在书写、建构一个“乡村的/贝都因的/非现代的”“他者”的同时,也在向伊斯坦布尔的读者群体不断宣告着自己“城市的/奥斯曼的/现代性的”归属(Minawi,Losing Istanbul,118)。因此,与其说萨德克的《撒哈拉游记》是对“他者”的客观民族志书写,毋宁说是写作者自身对于“阿拉伯人”认同焦虑的一种文学投射。在1904年的阿比西尼亚之旅中,萨德克在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增添了“种族化”(racializing)的话语,因而变得更加复杂。与黑人土著打交道的经历,使他把自己归类为具有文化优越感的“白人”(Whites);这一身份认同,自然也适用于远在伊斯坦布尔的潜在读者——即一般意义上的奥斯曼人。这位外交官在其记述中,将一切异质文化实践——无论是饮食习俗、价值观念还是社会风尚——都简单归因于某种本质化的种族特性,将其武断地等同于与肤色直接关联的蒙昧、迷信与非理性。尽管在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档案体系中,并不存在以“种族”(race)为基础的系统性分类架构,它也从未成为帝国治理中人口管理的核心原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种族主义”(racism)成为全球化现象的十九世纪,奥斯曼人对这一观念是完全免疫的。在当代奥斯曼史研究中,学者们普遍主张审慎对待“阿拉伯人”(Arabs)、“土耳其人”(Turks)等族裔-种族化标签(ethnoracial markers)的阐释效力,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尚未完全兴起的历史阶段(Minawi,Losing Istanbul,12.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简要学术评述,参见陈功:《十字路口前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上海书评》2022年四月第4期)。然而,在本书的作者看来,在一战之前已经出现更早期、非正式的族裔-种族区分潮流。因此,阿拉伯裔-奥斯曼人经历的被边缘化感,并不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之后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地方政治家所虚构的。它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而在1908年革命之后,特别是在革命的承诺落空之后,这一进程才真正浮出水面(Minawi,Losing Istanbul,12)。
第七章与尾声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在第七章中,写作的焦点再次落到了莎菲克身上。在经历了革命带来的动荡之后,莎菲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议会中担任叙利亚代表;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并领导阿拉伯政党活动,以对抗议会中长期存在的“反-阿拉伯”倾向。在这一时期,语言、文化、政治身份等敏感问题在公共舆论中得到了热烈讨论。尾声部分主要谈到了莎菲克与萨德克政治生涯的终结,以他们为代表的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主义者如何从历史舞台上谢幕、退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一战期间及之后所经历的命运:阿宰姆扎德家族的成员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国境线的两侧,各自在某个远离伊斯坦布尔的地方,分别讲述着不同版本的家族故事。
在本书的标题中,作者把这一代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称为“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s)。中国读者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之类的词汇不会感到陌生;然而,当它们出现在一个受到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压力之下的非西方语境中,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含义又有所不同。那么,当奥斯曼史学家提到“帝国主义者”的时候,他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汀·M.菲力欧(Christine M. Philliou)在《帝国的传记:在革命年代统治奥斯曼人》(Biography of an Empire: 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一书中追踪了斯蒂芬诺斯·沃戈里德斯(Stephanos Vogorides)的政治生涯,揭示了沃戈里德斯——一个奥斯曼法纳尔人(phanariot,斯蒂芬诺斯·沃戈里德斯的原出身为保加利亚人)——是如何在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的政治动荡中独善其身,之后又再次顺利地进入帝国的行政中心(Christine M. Philliou,Biography of an Empire: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菲力欧指出,与沃戈里德斯相关的学术研究长期受到双重边缘化:在奥斯曼史学范式下,他被简化为帝国官僚机器中的一个普通构件;而在希腊、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史学叙事中,他又被妖魔化为出卖民族国家利益的叛徒(Philliou,Biography of an Empire, xxi -xxii)。换言之,沃戈里德斯生平的“未受关注”,恰恰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超越了书写“民族主义史学”的一般边界。而当今的奥斯曼史家已经不再站在民族国家的“历史终点”,向过去投以“回溯性”的目光;而是把个人的行动,立场,以及身份认同嵌入与帝国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网络当中,打破“多元帝国-民族国家”的单线程叙事。“民族国家”对帝国而言,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民族主义”对个体来说,也不是一种绝对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标题中的“帝国主义者”一词象征着“民族主义史学”的对立面,其深层意图在于强调奥斯曼帝国认同所表现出的持久韧性(resilience)(Hasan Kayalı,Imperial Resilience:The Great War's End,Ottoman Longevity,and Incidental N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1)。这一学术立场直接呼应了著名奥斯曼史学者M.许克吕·哈尼奥卢(M. Şükrü Hanioğlu)发出的号召:要超越以“目的论”为导向的晚期帝国史书写(M. Şükrü Hanioğ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这一概念也被置于一个全球化语境中加以考虑——在作者看来,莎菲克、萨德克等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实质上属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帝国主义者”(global imperialists)圈层。然而,这一论述产生了一个语义上的危险:那就是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与非西方世界“防御性”的帝国主义——以及它们背后各自的倡导者——混为一谈。针对“帝国主义”一词所暗示的丰富内涵,殖民主义理论家阿尼亚·隆巴(Ania Loomba)指出,在谈论“帝国主义”的时候,必须把它与相应的历史进程相联系(Ania Loomba,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London: Routledge, 2005,26)。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不仅接受了西方化的教育,掌握多门欧洲语言,而且熟知西方文化;其中一些成员更是直接参与了各种外交事务,因而普遍具备了“全球性”的视野、知识与个人体验。然而,尽管欧洲的习俗在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被认为具有“普遍性”,或者是可以作为“一切的标准”(Minawi,Losing Istanbul,38)。因此,与“全球的”帝国主义者(globalimperialists)这一定义相比,笔者认为,“世界主义的”帝国主义者(cosmopolitan imperialists)一词也许更能区分阿拉伯裔-奥斯曼政治精英与其西方同僚在政治处境上的根本性差异,以及他们在智识上与西方文化之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从方法论层面上来讲,“帝国主义者”一语也展现了一种“微观史学”(microhistory)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相结合的视野,可以视为奥斯曼史学家探索如何写作“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一次有益尝试。一部分历史学家把“微观史”归类为“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 认为其主要特征是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来揭示那些长期在历史记录中遭到压抑的“声音”(Andrew I. Port,“History from Below,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and Microhistory,” i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Second Edition,ed. James D. Wright,Elsevier, 2015,108-113)。无论是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笔下的弗留利磨坊主——梅诺基奥(Menocchio)——的荒诞宇宙观(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trans. 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还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精心重构的真假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案件(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其中的主角都是隐匿在“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下无足轻重的“小人物”(individuals of no significance)。与这些相对早期的微观史研究相比,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的《帝国的内在生活:一部十八世纪的历史》(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书则在时间和空间上展现出更为广阔的视野。罗斯柴尔德卓有成效地运用了“帝国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s of empire)这一概念(Rothschild,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2),也就是处于社会中层的个体(“middling” social actors)如何通过通信、期望,以及家庭和职业网络与跨越帝国边界的多个事件相连接,与国内外不同社区进行互动。然而,即使在罗斯柴尔德“社会中层”的视角下,莎菲克与萨德克也远远算不上“合格的”微观史研究对象——毕竟他们不仅出身于显赫家族,供职于中央政府,更是直接卷入了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本书在选择莎菲克和萨德克二人作为主角时,似乎就已经偏离了作者自己所声称的“微观史方法”(microhistory methodology)(Minawi,Losing Istanbul,15)。然而,一旦更深入地考虑“究竟什么是微观史”这一问题,我们或许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因为,微观史本质上并不等同于“人民的历史”。微观史学正式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这一历史学派明显地流露出在两极化秩序崩塌前夜的不安情绪,警觉于政治、社会甚至文化危机的初步迹象。它推动历史学家关注“比较小的尺度”,深入研究历史现象的内部,通过抽丝剥茧地观察,识别出表面上不易察觉的重要细节;在细致入微地审视案例、事件、地点、物品和个体的过程中,提出更为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决定微观史本质的,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事件所具备的“微观特性”(microness),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显微镜式”的阅读与分析,突出相关的问题与事实(Giovanni Levi, “Frail Frontiers?”Past & Present,no. 242, Supplement 14,November 2019: 37–49)。如果按照这一观点去理解本书的“微观史路径”,那么米纳维教授实际上是“……从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到显然关键的事件,目的是通过人们生活中的亲密细节,唤起一个完整的世界”(Levi, “Frail Frontiers?”, 37–49)。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本书的叙述范围仅限于两位主人公的活动空间与人生轨迹;相反,作者更宏大的抱负实际上在于将“微观”的视角置于“全球史”框架中。对于任何尝试书写“全球微观史”的学者而言,如何妥善处理“微观”与“宏观”这两大看似矛盾的“研究尺度”,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就全球史的研究方法而言,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种是对在时间与空间上延展的现象的研究,强调表面上不同情境之间的关联性,通常采纳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但同时否认民族国家在其中的中心地位;第二种则侧重于连接不同文化与实践的网络。为了弥合“空间”尺度上的差异,米纳维教授借用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与“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概念。沿着第一条全球史路径,作者强调了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主义精英在微观层面上的“惯习”是由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空间”(global social space)所塑造,又反过来决定了个体如何感知“社会空间”,从而较为成功地调和了“微观”与“宏观”两大空间尺度。尽管作者似乎未能触及“微观-宏观”层面上更为本质的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张力,但是考虑到奥斯曼研究与微观史、全球史之间长期的低频对话,把奥斯曼史纳入“全球微观史”方法论对话的尝试,在史学范式上的确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米纳维教授也没有解决一个微观史家们需要面对的常见困境——“代表性”问题(question of representativeness)。一直以来,一些批评家对于微观史家笔下的“个案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某一类群体心存疑虑(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Routledge, 2013)。同样地,莎菲克、萨德克的个人行为、经历与“惯习”在“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奥斯曼帝国主义者”这些圈层中到底有多少代表性呢?另外,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族裔-种族化观念在一战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当中已经存在;然而,在把“个体性”观念推广为“社会性”思潮的过程中,作者的论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
当然,本书还有其他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在重构个人经历与“惯习”的过程中,作者采取了对官方档案的“逆向阅读”(read against the grain)与对个人旅行笔记的“正向阅读”(read along the grain)并行的解读方式。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再展开分析。总体来说,《失去伊斯坦布尔》一书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在专业性的史学关切之外,米纳维教授流畅且优美的笔触同样引人入胜,向读者娓娓道来一个“失去伊斯坦布尔”的悲情故事,再现了一个属于阿拉伯裔帝国精英们的“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